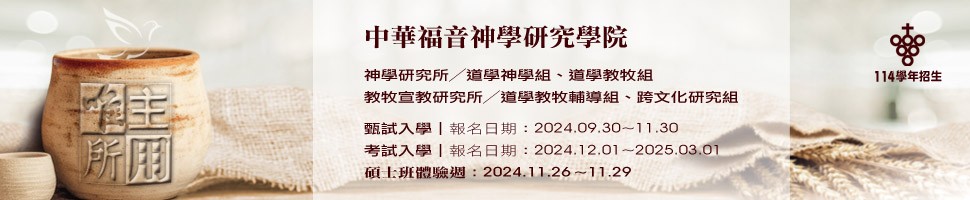迎接超高齡社會,「非正式照顧者」需求知多少(上)
檢舉

我國目前照護服務涵蓋率偏低,所倚靠的外籍看護也正逐漸移往日本。面對超高齡社會的趨勢,職業照顧者的數量總是跟不上照護需求增加,因此讓「非正式照顧者」成為社會上的正規照顧資源,構成社區照顧網路,才可能緩解照顧壓力。
你是否曾聽過以下這些情形?長者因孩子大了搬去外面住,家裡剩下夫妻二人。某日,丈夫到台北探視父母,太太竟心臟病發身亡、未及發現救援。還有獨居長者,兒女在國外,體能雖未達到政府評量的「失能等級」,實際上卻隨時可能摔倒,需要人看顧。還有「初老」兒女照顧患病末期的「老老」父母,子女獨自承擔疲累重擔,內心竟深怕長輩活太久。
教會也會遇到需要關心的獨居長者。筆者聽過有一戶人家,長者罹患大腸癌很痛,子女和熱心鄰居一再送來食物,怕長者營養不夠而一直硬要她吃,更增添了長者痛苦;這反映了我們都需要更多長者照護的知識。
另外一個例子是,教會中有一位獨居失智的老媽媽,她兒子從美國回來協助處理事務,但老媽媽認為兒子是來要財產的。孩子依法是親屬,比牧師更有權討論媽媽的情形。牧師該用什麼立場關心這對母子?在可見的未來,這些需要關心的長者將倍數成長,教會需要更多裝備來關顧。
超高齡社會 照顧資源不足
我國於2018年邁入高齡社會,預估2026年就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國發會預估2025年)。據衛福部三年前所做的《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灣社會的健康老人占了六、七成,衰弱失能占三成,而在老人總數增加時,後者自然增加更多,而且目前照護服務涵蓋率偏低,約僅兩到三成左右。
政府設法支持需要服務的對象,盡可能支持他們自主,或可緩解需求。然而根據政府估計,2026年有照護需求的人可能高達100萬,低估也有92萬人。我們的居服員儘管因勞動條件改變而增加,但仍因少子與社會價值觀因素而有極限。照服員總數從2018年的三萬五千人,到了2026年又會有多少人呢?
至於機構照顧,因居服員的薪水和服務制度等因素,導致不少人離開照護機構,形成外勞占絕大多數的局面。被照顧的老人,講話外勞聽不懂;照顧者講的話,老人也聽不懂。更別說照顧機構人手不足,導致一人照顧多人,或甚至得綑綁灌食。
照服員數量比不上照護需求
在北歐國家,荷蘭社會文化規劃辦公室SCP及環境評估署PBL研究人員研究指出,2018-2030年超高齡社會的趨勢(http://digitaal.scp.nl/ouderenzorg/),包含照顧需求急速增加,但公共照顧資源不可能對應滿足。也發現,職業照顧者的數量總是跟不上照護需求的增加,造成照顧者疲於奔命的窘境。
加上新一代老人的教育背景提高,連帶的照顧方式也將改變。從照顧者事必躬親,轉變為支持老人自我照顧。然而偏鄉或低教育程度的老人則可能成為弱勢族群,因為他們缺乏取得資訊的能力,而且年輕人外流。未來的科技雖可以幫助人,但仍有一定的極限;尤其是生活需要與人際互動帶來的慰藉,才能讓人感到自己是被了解的。
面對這樣趨勢,勢必建立「非正式照顧者」成為社會上的正規照顧資源,協同職業照顧者、家庭照顧者,構成社區照顧網路,才可能緩解照顧壓力。
荷蘭發展出成熟照顧體系
荷蘭已經有國家級研究組織倡議,還有專屬網路資源開始培養此體系人才(https://www.mantelzorg.nl/) ,甚至協助非醫療背景的民眾,提供通俗而先進的自我導向學習資源,來裝備民眾如何協同專業照顧(https://www.zorgvoorbeter.nl/)。
這些政策訴求,不但要建立非正式照顧體系,而且投入者要學習了解老人的期待和各種落實的可能性(包括與老人同共住),並將規則納入法規。期待幫助長者能不搬去機構就盡量不去,以免老人損失原居住社區的資源連結。
荷蘭已發展出成熟的行政支援型志工,例如,在一千兩百個失智照顧農場中,由許多社區民眾(例如賣場工作人員),抽空排班開交通車,固定接送失智老人們回家,或有各種關懷組織幫助社區民眾。
但是荷蘭接下來想發展更系統性的照顧合作方式,因為接下來的照顧需求「多的不得了」。目標是全力支持長者自我照顧,來降低正式照顧需求,而剩下的就需要用非正式照顧,協同正式照顧來因應。
納入非正式照顧者的必要性
台灣也有類似的處境,而且我們的少子化更嚴重,台灣所倚靠的廿五萬外籍看護,正逐漸移往日本,雖然也可能回流,但可能要求更高的薪資。因此,外籍看護是否能成為未來可靠的照顧資源,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所以我們必須更重視上述各角度如何影響未來的照護服務布局。以下特別聚焦「非正式照顧者」的發展,因為這是必須,卻又要跨過許多挑戰,才能成為可靠的補充性照顧支持資源。
所謂「非正式照顧者」,主要指未以照顧服務為職業,也非家庭照顧者的「其他可提供參與支持的社區民眾」,例如衛生所長年已有的志工隊,還有社區社團、退休者、休假的上班族,但要能透過組織化,使參與者個人有彈性,而組織能穩定排班出支援照護人手。
非正式照顧者不支薪,否則失去緩解國家預算的意義,也具有某種參與的自由度,以維持樂於參與和各盡所能的精神。雖個人有參與自由度,但為了維持社區穩定輔助的照顧能量,可能透過一定程度組織化,和有限度教育訓練確保照護素質和倫理,讓調度者安排。
國內過去也留意到「非正式照顧者」,例如較早的衛生所志工大隊,搭配社區護理師共同從事居家訪視、公衛計畫、疾病防治。這要看各縣市積極度與民情文化。後來台灣人口結構老化,政府逐步從大溫暖、長照十年計畫、長照2.0發展許多新的服務資源,來支持在社會變動中更有品質的老年生活,以不同失能層級對應不同的給付照顧,並推廣資源連結,而於非正式照顧者發展有初步成果。
晚近國健署推廣引進「慈悲關懷社區」,提供社區緩和醫療照顧資源,因為安寧需求增加,適當陪伴支持可能增加生活品質。其策略是直接於多個社區針對初老推動,先從生命教育活動開始。後續有待觀察。
民間團體推動志工服務
民間也覺察非正式照顧體系必要。如嘗試各種型態「時間銀行」鼓勵服務,在少數歐洲高度公民素養的國家逐步打下基礎。國內則因項目釐清和回饋公平與可靠性,迄今未能建立足夠普及模式。
宗教界也在努力。如台灣教會界推動的「第三家庭」,意思是從人出生到就業約前25年是第一家庭;自己成家養育子女約第二個25到30年是第二家庭。第三家庭是老後由老老互助,形成如同家庭的關係。
透過教會、社區及社團,針對未必符合長照服務標準、但有實際需要的長者,組織關懷體系,並藉發展過程中的教育訓練,同步鼓勵初老民眾投入關懷並預備優質老年生活,培養超高齡社會公民素養。還有宗教團體就本有之關懷據點,進行實驗性的緩和醫療訪視。
但宗教團體難免牽涉信仰理念,如何保有開放性,讓服務可及並得到民眾接納,需要磨合。若一個宗教團體想要發展超高齡社區關顧,還要看是否會友同屬一社區,否則要這些距離遠近不定的會友,形成隨時到府的網路也不容易。
這些民間非正式照顧者計畫,未來要如何與正式照顧體系接軌,還很難說,但高齡長者的照顧需求,已經擺在眼前。
相關閱讀:迎接超高齡社會,「非正式照顧者」需求知多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