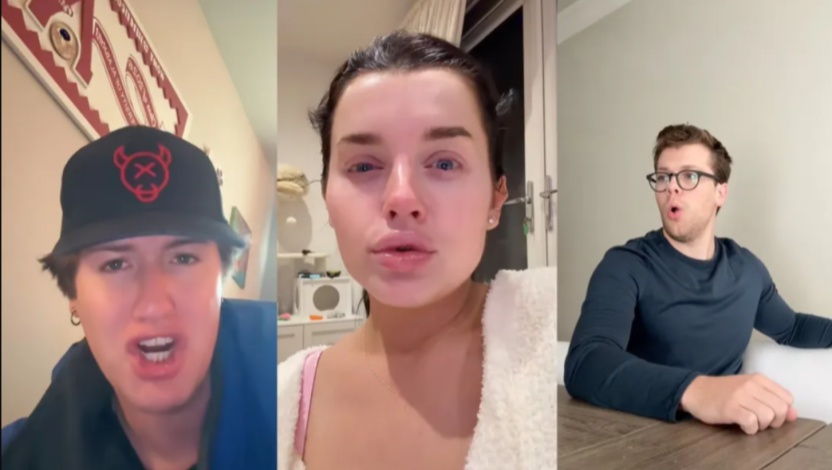◎盧怡君(中原大學應用外語系教授)
我們的火車誤點了。
這班火車從布達佩斯的德利車站(Budapest-Déli)出發時就延宕了將近20分鐘,原本預計傍晚八點會抵達克羅埃西亞首都札格拉布(Zagreb),但是在行經巴拉頓湖區(Balaton)時,夕陽就已幾乎浸入湖水。火車沿著湖的南岸緩緩行駛,每隔幾公里就停靠一個湖岸小鎮,儘管天色漸暗,從車窗望出去,仍可見到一群一群度假的觀光客,身著鮮豔的泳衣在初夏溫暖的湖畔戲水。
淡淡的落日餘暉從車窗傾灑而入,我一直倚著半開的窗子看電子書,直到最後一束陽光也消逝在地平線上,包廂裡一片昏暗,才揉著疲憊的眼睛,起身到外面走道上透氣。包廂裡除了我和先生還坐了兩對年輕男女,六個座位都坐滿了,感覺挺擁擠的。

從溫暖湖區駛向夜幕沼澤
2022年六月,歐洲人在被疫情禁足了兩年之後,就像放飛的鳥兒迫不及待衝出牢籠振翅高飛,不論到哪裡,每班車上都坐滿了出遊的旅客。這兩對年輕男女看起來是東歐人,一路上低聲談笑、一面分吃著各自包包裡的零食,神情親密友愛。四人各自帶著簡單輕薄的背包和一瓶水,如同我和先生向來旅行的習慣──行囊帶得少,路才能走得遠。
這是東歐老舊的包廂式火車,我趴在走道上敞開的窗戶往外看,車子在駛離巴拉頓湖區之後立即折而向南,進入匈牙利西南部的叢林沼澤區。經常坐火車在歐洲各地旅行,並非沒見過叢林或沼澤,但這片叢林沼澤實在太遼闊、太原始、太荒涼、太陰森了!
一會兒,火車開始像走吊橋一樣忽高忽低的上下擺動,在沼澤地上波浪狀前進,彷彿有一段鐵軌陷入了沼澤,然後又再浮上來,再陷入、再浮上來……每一次波動都令人毛骨悚然,似乎列車就要被沼澤吞噬了。好長一段路,火車在荒煙漫草中簌簌前進,我有一個衝動想走到最前方的駕駛廂,確認駕駛員真的看見前方延伸的鐵軌。
四野杳無人跡,連隻歸巢的雀鳥也無,昏黃的天空漸漸被深藍的夜幕包圍,不久,窗外只剩下朦朧的樹影。走道上的小燈亮起來,透過玻璃門窗,看到包廂裡那四個年輕人仍在指手畫腳的談天,儘管車廂破舊、路途顛簸、叢林沼澤驚險,有知心的朋友結伴旅行,在那小小一格車廂中,天地仍然無限美好。

掀起過境邊界恐懼回憶
在離開匈牙利進入克羅埃西亞之前,火車停了下來,這一停竟停了30分鐘。這裡是匈牙利的邊界小鎮Gyekenyes,過境的乘客必須出示護照。
我對「過邊界」向來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原因要追溯到1989年年初,我第一次從當時的西德乘坐巴士進入東德。在東西德邊界上,全車乘客只我一個被叫下車,站在冰雪紛飛寒風徹骨的荒原上,我永遠忘不了那個魁梧的東德軍官,揮舞著我那本扉頁上寫著「持此護照不得前往共產國家」的台灣舊護照、對我跳腳咆哮的恐怖模樣。
回到現在,為了轉移不安的情緒,我試著打電話給預訂好的札格拉布民宿,說火車誤點了,恐怕要遲兩個鐘頭才能抵達。電話還沒講完,包廂門被打開了,三個身穿制服配戴武器的彪形大漢擠在門口,其中一個探頭進來,用出操口令的音量說:「邊界警察,檢查護照!」
我和先生立即將上面印了大字"TAIWAN"的新護照遞給那位帶頭警官。四個年輕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神,慢吞吞的從包包裡拿出護照,兩本深藍色、兩本暗紅色,分別交給另外兩位警察。我瞄了一眼,若是沒認錯,深藍色的是烏克蘭,暗紅色的是俄羅斯。
那個帶頭警官把我和先生的兩本護照翻過來、翻過去,摸摸這個角、拍拍那個角,仔仔細細「檢查」了一番,又抬起頭來盯著我們打量了好一會兒。
有什麼問題嗎?我們護照裡附有德國長期簽證,他看得懂德文嗎?天黑了,這個僻處邊疆叢林蠻荒之地的山寨老大不知道會對我們怎樣,他該不會沒收護照吧?心裡正嘀咕著,卻見到一抹微笑逐漸在老大的臉上蕩漾開來,原本森冷的眼神也變得清亮和善。「台灣啊,很棒很棒!」說著在我們的護照內頁使勁蓋上一個章。真難以置信,這位匈牙利的邊界警察在歸還護照時,我似乎看到他還恭敬的向我們行了個禮,再昂首闊步離去。

月台滿是長串下車旅客
才剛放下心吁了口氣,一個沒穿制服的大漢直接走進包廂,開始嘰哩咕嚕的向那四個年輕人問話,四個人也嘰哩咕嚕的回答。之後,他轉過頭去用「匈奴語」向包廂門口那兩位警察轉述,原來他是翻譯員。然後出乎意料之外,四個年輕人從座位起身,拿起各自的包包和水瓶,跟著邊界警察下了車。
啊,不對,不只他們四個人,在蒼白的路燈映照下,我看到月台上站了長長一排下車的旅客,旁邊還有十來個穿制服的警察,每個警察手上都拿著厚厚一疊護照。此時我才恍然大悟,這列老舊的東歐火車上坐滿了難民,不是遊客。難民在月台上挨擠著,每個人都只帶著簡單的背包,逃難是不能帶大行李的。
六月中,俄烏戰爭已經開火近四個月,最初從烏克蘭被送走的都是老弱婦孺,北約無條件的收留安置這些難民,只要出示烏克蘭護照就可以免費搭乘歐洲所有的陸上大眾運輸。戰火不歇,接著年輕人也開始逃離,不只烏克蘭,俄羅斯的年輕人更千方百計要離開俄國。人民何其無辜,因為主政者的無知顢頇與野心,多少人的家園被摧毀、人命輾轉溝壑,多少親人被迫分離。
分道揚鑣的身影沒入黑暗
我的眼光始終緊追著這四人下車的背影,雖然素昧平生,語言也不通,好歹我們在一格小小的包廂裡,一起穿越匈牙利的城市村莊、田野湖泊、叢林沼澤和荒原,一起度過了還算溫馨的幾個小時。他們一路上笑語如珠,幾乎忘記自己在逃難,又是來自兩個正在砲火相向的敵對國家。然後,我看到兩個警察把他們帶離開月台,四個人分開了,兩個走這邊兩個走那邊,四人不斷回頭跟同伴揮手,身影逐漸沒入陰暗、路燈照不到的地方。
火車繼續前行,沒多久到了克羅埃西亞的邊界小鎮Koprivnica。剛才是「出境」,現在才是「入境」,同樣的邊界戲碼又要再重演一遍!有了剛才的經驗,我已沒那麼心慌,卻想不到克羅埃西亞的警察比匈牙利的更友善、積極。「台灣來的哦,歡迎歡迎!」警察豎起大拇指比個「讚」,然後拇指指向自己胸部,一副「有什麼事找我就對了」的神情。
怎麼回事?就算疫情期間難得有亞洲人在當地旅行,也不必這麼客氣啊!其實大家心照不宣,俄烏開戰後,只要和德國朋友一聊天,他們一定把台灣跟烏克蘭相提並論。我們三天之後會離開札格拉布繼續前往盧比亞那(Ljubliana),我很好奇斯洛維尼亞的邊界警察面對台灣護照會有什麼反應。
這次火車沒停太久就開動了,沿著鐵軌滑入無邊無際的黑暗,現在窗外什麼也看不見,我開始後悔稍早天色還亮時,沒多捕捉一些沿途風景,在行萬里路的當下竟然還埋頭讀萬卷書,真蠢!書本什麼時候都可以看,而這一段旅途的許多風光卻給錯失掉了,誰知道還有沒有下一次的相遇。窗外逐漸出現稀落的路燈,昏黃的燈光下出現同鐵軌平行的清冷馬路,這班列車的終點站已然在望。
相關文章:星空下的札格拉布音樂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