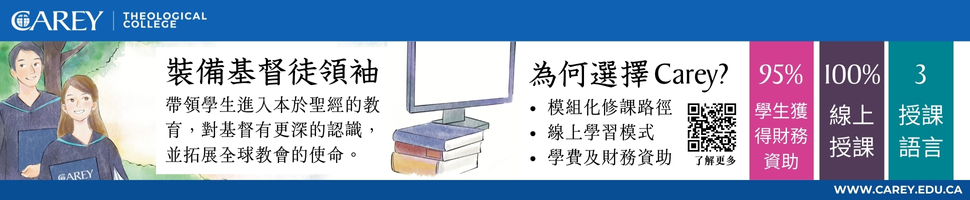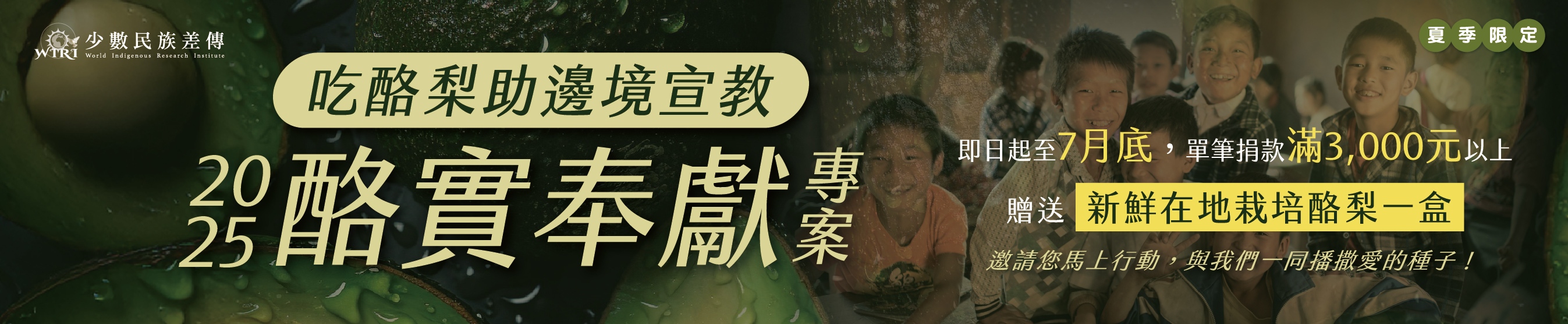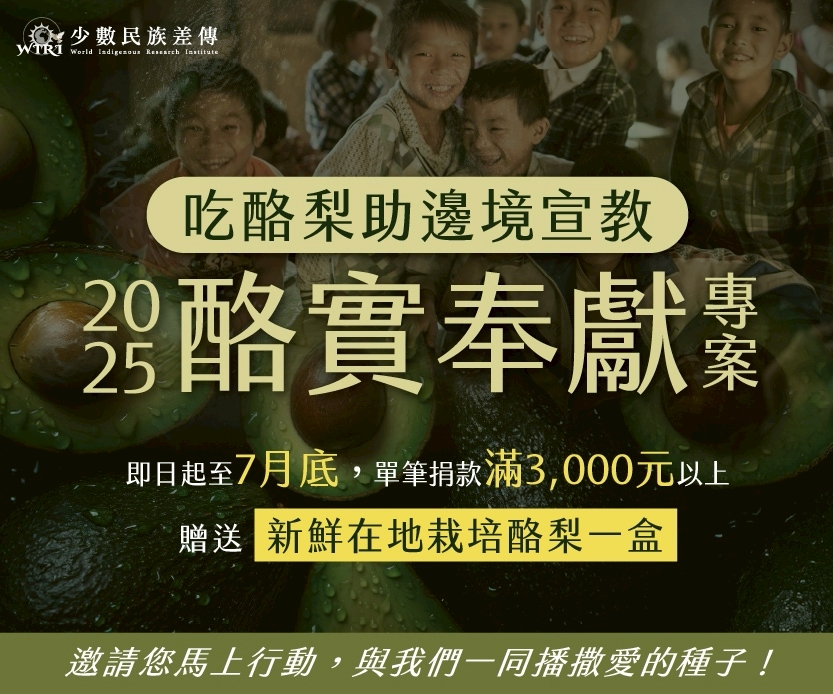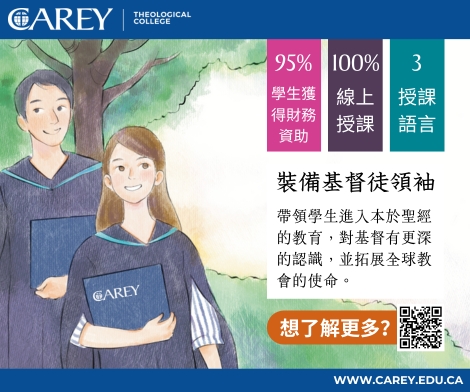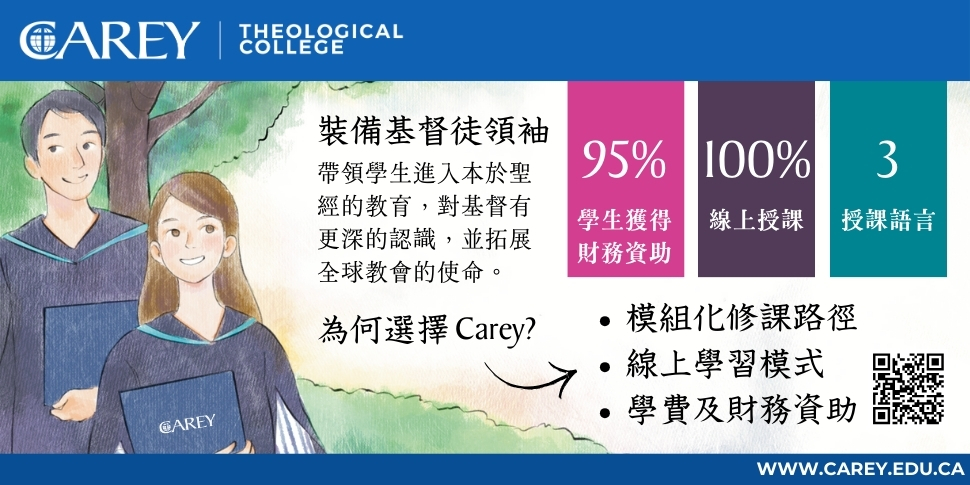◎魯瑪夫牧師(WIRI少數民族差傳創辦人、中原大學副教授)
提到運動賽事,讓人不禁聯想到原住民族菁英在體育競技中的亮眼表現,尤其在奧運等高曝光的國際賽場,更常看到原民選手的身影。五月初,我帶著學生參加由台灣八大布農行政區輪流舉辦的布農族運動會,這次並非我們自己組隊報名,而是結合課程規劃的實地體驗。
現場約有布農族人5000人聚集,每個隊伍皆是技能方面的重量級,各個有備而來,一入場就氣勢震天。這麼多族人從不同地方來到花蓮聚集,見了面更是熱絡寒暄,互相親切打招呼,談笑風生,所以比賽還未開始,氣氛就已熱鬧不已、笑聲連連。開始後,周遭加油之聲不絕於耳,含混著落敗的惋惜聲及勝利的歡呼聲,賽場外和賽場內一樣精彩,一樣汗流浹背。
布農族運動會 文化與體能的雙重競技
不同於我們熟悉的運動賽事,布農運動會的比賽項目,除了拔河,還包括鋸木、背重物等,這些源自傳統生活的競技,對一般漢人來說,背重物竟也能成為認真比拚的項目?或許感到不可思議,但對布農族人而言,這正是日常。

鋸木頭和背重物反映了族人平常生活的樣貌,布農族靠山吃山,花費時間和體力取得山裡的自然資源是傳統生活的家常便飯。不僅要把樹砍倒,還得把木頭抬下山或抬回家。即使現在有汽車載送,減少了很多背重物的過程,但是砍完之後,必須把木頭抬上車、抬下車,回到家還要把木頭再劈成更小塊的木頭以便收藏使用,其實整個過程都是非常耗費力氣的。
生活即訓練 母親與部落婦女的力量
看著賽場上額頭汗如雨下、衣衫濕透的族人,努力原地重現辛苦的傳統生活,又鄰近母親節,我想到母親以前跟父親一起上山工作,做的都是這些極為粗重的工作,即使她懷孕了,也在幫忙搬石頭整地、劈木頭等等。因此我母親年輕時,搬重物對她來說不是太難的事,如果當時有舉辦這種傳統生活的比賽,她去參加說不定能夠擊敗男性也說不定。
另一方面,我唸研究所時,曾經帶當時的同學去部落參加部落的運動會,其中一個項目是排球比賽,使用的球並非正常的排球,而是直徑50公分以上的沙灘球,雖然皮質比較柔軟,但是體積很大,重量也重,如果拍打的人手勁很大,被砸到確實滿痛的。
我同學看到那麼大顆的球,猶豫著要不要上場,便問為何不用正常排球?部落婦女說道:「那個球太小了,看不清楚,打起來沒有感覺」後來一位同學,被一個部落婦女拍過來的球砸中耳朵,他說他感到瞬間耳鳴,沒想到女性的手的力道可以把球拍的這麼遠、這麼高,有如此驚人爆發力。被這球砸到之後,這位同學二話不說下場休息。
部落女性在付出勞力與忍受痛苦這方面,確實有卓越之處。體能方面是因為生活環境的需要,幾乎每天都在搬重物的重量訓練而逐漸累積起來。然而不同環境有各自生活方式,每一位認真的母親,透過自己的能力養育家庭,都值得被尊敬並享受尊崇的母親節。

從比賽到傳承 布農族運動會的文化意涵
回到比賽,我們平常在電視上觀賞正規的比賽節目,見到諸多原住民同胞表現優異,無不欽佩他們的毅力。那種鍛鍊的過程、忍受的痛苦絕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國際賽事的場合,大體上觀眾似乎比較嚴肅看待,對於輸贏也是心懸一線、非常在意,屬於攸關榮譽的心態。
原住民運動會,至少布農族運動會的目的,除了團結各地族人,以及增添趣味性外,還能夠提醒並且傳承年輕族人傳統的生活方式,讓年輕族人以具有趣味性的方式體驗傳統生活。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說:「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以此勉勵人做事情不可沒有目標,一生的目標決定了人生方向。科學訓練促使選手邁向更高榮譽的過程,選手拼命晉級獲得參加的資格,窮盡體能訓練自己,為要爭取殊榮與冠冕。布農族運動會的選手們,訓練的場地在山村部落,日常幹活的無形之中,身體適應各種粗活不叫苦,是他們訓練的方法。
族人的傳統技能賽事,乃集全體族人之力,表現了傳統生活每天都在用盡力氣、實實在在的生活,以及族人內在的凝聚及認同;族人的傳統生活競賽上,所盡的力,盡的是老一輩族人傳承智慧和忍耐的力,不是奮力爭取你輸我贏的力。
兩種氣氛十分不同的賽事,都望向自己的目標,經歷著日日的磨練,顯耀出非凡的光華。基督徒也正在場上比賽:「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哥林多前書九章24節)信仰生活是新造的人與老我的比賽,靠著基督每日勝過一點老我,逐漸鍛鍊出足以照亮黑暗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