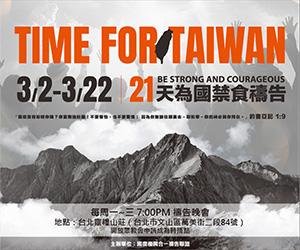◎語聆
1972年9月5日,在德國慕尼黑的奧運會選手村裡,清晨天未亮,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運動員正在熟睡當中,或者醉醺醺地預備就寢時,8名來自巴勒斯坦激進派組織「黑色九月」的武裝分子,輕鬆翻越了圍牆,迅速潛入以色列代表團駐村,當場射殺2人,並挾持另外9位人質。他們要求以色列當局立即釋放數百名巴勒斯坦囚犯作為交換條件。
史上首度恐攻轉播吸引全球矚目
電影《九月五日:人質危機》以新聞事件作為敘事起點,但是內容並不聚焦於人質、武裝分子或者中東政局,而是探討媒體在報導危機事件中所面臨的倫理困境。由美國ABC電視台體育部門總裁阿利奇(Roone Arledge)領軍的採訪團隊,原本被派到慕尼黑轉播擊劍、拳擊等奧運賽事,卻意外成為歷史中的一部分。
因著人質事件的展開,他們首度即時轉播突發的恐怖襲擊。那場報導當時吸引了全球9億人觀看,也成為電視史上觀看人數最多的一次現場轉播。
媒體全天候報導恐怖襲擊事件,在2025年的今天已經屢見不鮮,但是對年輕一代的觀眾而言,或許很難想像半個世紀以前,人們第一次透過電視現場轉播,「見證」歷史事件的情景。執導過《驚爆焦點》、《郵報密戰》的瑞士籍導演費爾鮑姆(Tim Fehlbaum)以驚悚片的節奏帶觀眾重新回到這場1970年代政治、歷史與新聞倫理的混亂當中。
「作為一名在媒體工作的創作者,我覺得自己可以藉這部作品,針對當今這個複雜的媒體環境,發出一些特別具有現代意義的聲音。」導演提姆‧費爾鮑姆說電影敘事圍繞在一個封閉空間深具挑戰性,製作團隊根據當年原始藍圖和老舊設備,細緻重建了主控室,真實呈現當時像壓力鍋一樣的工作場景,但是也因此將觀眾瞬間帶入那場即時轉播的現場,經歷播報團隊當時面臨的壓力與掙扎。

呈現新聞背後攸關生死倫理抉擇
電影的核心角色是由約翰‧馬加羅(John Magaro)飾演的ABC導播梅森(Geoffrey Mason)。起初他是個不起眼的小人物,帶著一副「好好先生」的面孔,總是憂心忡忡。上司阿利奇一聲令下,他被推上火線,擔任主控室指揮的重任。
當阿利奇試圖抵抗新聞部施加的壓力,力保體育新聞對整場轉播事件的主導權時,梅森頓時成為故事主角。夾在上司、ABC新聞部與競爭對手之間,梅森每一次出現在銀幕上,觀眾都能感受到他內心瀕臨崩潰的掙扎與恐懼,深怕一個小小誤判會釀成無法挽回的巨大災難。
另外兩位關鍵角色是被臨時徵召協助翻譯的德裔實習生瑪麗安(Marianne Gebhardt),以及猶太裔紐約人、ABC體育部門營運主管巴德(Marvin Bader),兩人都對人質事件有強烈的個人情感,在影片中有充滿張力的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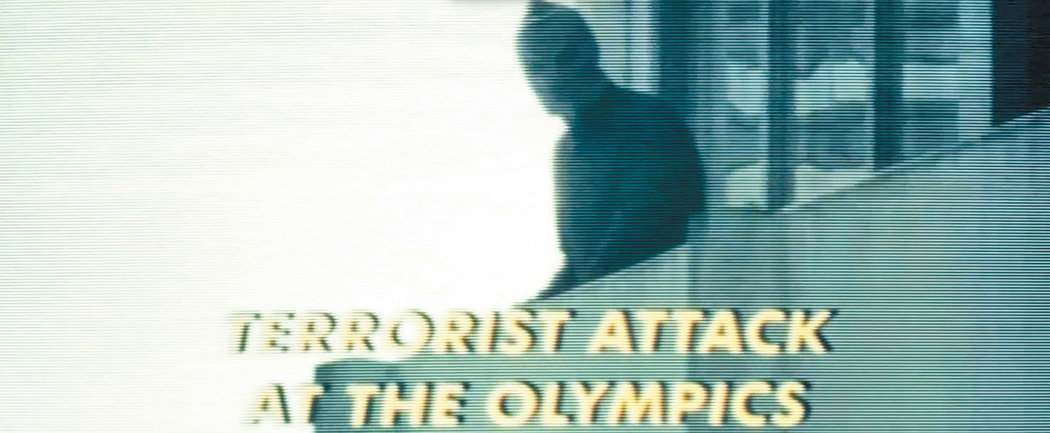
觀看此片,不能不聯想另一部20年前由史蒂芬‧史匹柏執導的《慕尼黑》,電影聚焦奧運恐怖襲擊事件後的報復行動,側重道德掙扎、報復與正義的灰色地帶。相較之下,《九月五日》選擇從新聞記者視角切入,關注媒體當天「如何成功地播出這場危機」。
紐約時報影評指出,電影中的記者角色通常被塑造成兩種極端:一種像《驚天大陰謀》(Allthe President’s Men)裡面正義凜然的英雄;另外一種是《血肉成泥》(Ace in the Hole)裡剝削他人苦難的反派。《九月五日》避開了這些刻板印象,跳脫新聞媒體常見的道德高標與自我讚許,冷靜而理性地剖析媒體這個行業的本質。
影片故事除了阿利奇之外,大多數記者都是腳踏實地,盡心竭力將新聞資訊即時傳遞出去的「好人」。然而,在轉播過程中,「每一處剪接、每一個精心構思的鏡頭、每一句播報的語調,媒體人也不自覺地以戲劇性的方式『包裝』這場危機,將恐怖事件化為一種讓人不安的娛樂消費。」
然而,《九月五日》的精彩之處,不僅在於它如何避免對新聞工作者的刻板化描寫,更在於它願意把鏡頭對準那些現場決策者的內心拉鋸與道德困境。在壓力下,這些新聞傳遞者,同時變成了倫理現場的第一線執行者。電影透過一連串發人深省的對話,讓觀眾得以窺見這場看似「技術性操作」背後,其實隱藏著許多關乎生死、價值與操守的選擇。
1.「我們可以直播有人正在被槍殺的畫面嗎?」
當導播梅森面對是否應該播出暴力畫面時,提出了這個道德上的疑問。
2.「他們知道全世界都在看。如果他們在直播中殺人,那這故事到底是誰的?是我們的,還是他們的?」
這是巴德向上司阿利奇提出的問題。媒體是否可能在無意中成為恐怖分子的傳聲筒?這句話挑戰了觀眾對新聞報導裡「誰在講故事」的認知。
3.「我們正在創造廣播歷史。觀看這次報導的人,比當初觀看阿姆斯壯登月的人還多。」
這句話突顯了這次事件在媒體歷史上的重要性,也引發了對媒體影響力的反思。

探討人們如何觀看他人的痛苦?
《九月五日》影片最讓人坐立難安之處,不在於畫面上是否出現血腥暴力的場面,而是它揭露了一個更幽微的問題──我們如何觀看他人的痛苦?
主控室導播梅森在壓力下被推上成為主角,他與團隊一邊努力在直播技術、資訊傳遞與新聞倫理間抉擇,另一邊也在無形中將這場恐怖事件包裝成「全球矚目的現場轉播」,引導觀眾如何「觀看」這起悲劇新聞。
媒體在即時報導過程中,將人們正經歷的「真實痛苦」轉化為銀幕上刺激的感官體驗時,讓觀眾不僅是旁觀者,也成了消費者。
當觀眾以「觀賞者」的姿態,凝視別人的苦難與恐懼,不禁讓人反思:我們是為了知情而觀看,還是為了刺激感官、被震撼而持續觀看?這不僅是媒體人的課題,也是每一位身處自媒體時代的觀眾需要面對的靈魂拷問。
當新聞真相與苦難,被聲量與畫面震撼感所掩蓋時,我們需要警醒:是否能夠懷抱同理心與公義之心看待別人的哀哭與絕望,我們內心產生的是憐憫,還是冷漠?是悔改,還是滿足?
聖經羅馬書提到:「要與哀哭的人同哭。」在這個視覺影像大行其道的年代,我們如何學習以愛和尊重來凝視那些破碎與苦難的故事,而不只是將其視為一場安全距離內的驚悚片或者茶餘飯後的談資,值得深思。

成為痛苦中的見證者與守望者
反思本片探討的新聞倫理議題時,腦中不免浮現1997年台灣社會發生的一起白曉燕命案,主嫌陳進興在逃亡期間,闖入台北市北投南非武官官邸,挾持官邸內一家五口為人質。
當時我人在香港,坐在主播台上報導這則新聞時,親眼目睹其他電視台為了搶快、搶「獨家」,完全忽視人質安危與喪失倫理操守:有主播與嫌犯進行連線,並現場播出通話內容;有主播直接詢問嫌犯:「你什麼時候要自殺?」;另位主播則要求陳在電話中唱〈兩隻老虎〉給孩子聽。也有節目主持人在直播中公布受害者母親的電話號碼,要求嫌犯撥打……種種匪夷所思的亂象,引發社會輿論撻伐,最嚴重的是媒體的不擇手段嚴重干擾了警方談判與追捕的行動,幾乎成為犯罪者「共犯結構」的一環。
從1972年的慕尼黑到1997年的台北,兩場危機雖跨越國界與時代,但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媒體是否仍能在混亂與壓力中堅守倫理,成為痛苦中真正的見證者與守望者?
耶穌曾問:「那人落在強盜手中,誰是他的鄰舍?」(參路加福音十章36節)這不僅是對一名律法師的提問,也是對每位媒體工作者與觀眾的提醒:當擁有話語權的我們站在鏡頭後,我們究竟是選擇站在資訊的對面,還是站在受苦者的身旁?
在這個以速度為王、流量至上的時代,媒體人,不應只是觀看者,更應是同行者。
(本片分級為限制級;本文由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