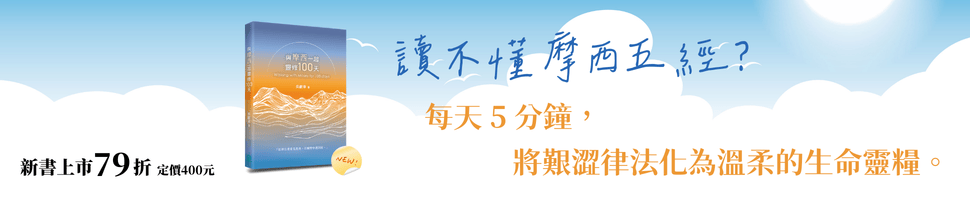【本報主筆】近年來,台灣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風暴。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罷免風潮」——原本作為民主監督機制的罷免制度,要用於罷免不適任的代議士;卻也在政黨對立之中,難以免於被當成報復的武器,不同陣營的彼此攻擊,造成社會撕裂、群體互攻、信任崩解。
在這場政治動員的浪潮中,許多教會與信徒基於理念而採取的公開參與,引起社會關注。然而,當牧者站上集會舞台、當教會成為動員網絡的一環時,我們也必須思考:教會在台灣的政治場域中,究竟應扮演什麼角色?教會是否要將信仰的道德資本投入黨派競爭,還是回歸上帝所呼召的「先知性使命」──在動盪的時代,作真理與和解的見證?
教會須拒絕被政治光譜定義
從聖經的脈絡來看,教會被呼召,不是作政權的顧問,而是作上帝真理的見證人。舊約中的先知——阿摩司、彌迦、以賽亞──並非配合政黨的方向,而是敢於在王面前說出「公平與憐憫」的信息。施洗約翰在希律面前直言無諱,使徒則宣告:「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使徒行傳五章29節)。
猶太思想家亞伯拉罕‧赫舍爾(Abraham Joshua Heschel)曾說:「先知的話,是黑夜中的呼喊;當眾人沉默,他卻呼喊;他是上帝借給受苦者的聲音。」(Heschel, The Prophets)
先知之所以說話,不是為了取悅權勢或迎合輿論,而是為了喚醒良心、傳遞上帝的憐憫。同樣地,舊約學者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指出:「先知性的任務,是滋養並喚起一種與主流文化不同的意識。」(Brueggemann, Prophetic Imagination)
因此,教會若要保持先知性,就必須拒絕被政治光譜所定義。它的力量不在於受歡迎,也不在於親近權力,而在於願意為真理作見證──哪怕要付上代價。
先知不是王的使者,而是神的信差
然而,信仰熱情被黨派政治吸納的誘惑始終存在,若是如此,教會原本屬於上帝的「先知性想像」(prophetic imagination)便逐漸麻木。布魯格曼警告說,當先知的聲音「被王權的意識所收編」(co-opted by the royal consciousness),它便失去哀傷、批判與盼望的能力;赫舍爾也提醒,先知「不是王的使者,而是上帝的信差」,他的痛苦來自於上帝的心腸。
假如教會為了靠近權力而交換這份呼召,就會失去兩樣東西:其一是見證的可信度──當教會被視為某一方的代言人,就再也無法向另一方傳遞福音的和解信息;其二是道德的自由──當教會被政黨綁住,就難以對自己偏好的那一方發出批判。
結果是悲哀的:教會不再承載上帝為不義而哭泣的心,而只是重複這世代的口號。歷史早已見證,無論是上個世紀曾與極權結盟的歐洲教會,還是被民族主義綁架的美國教會,當信仰成為意識形態的附庸,先知性便淪為宣傳。
在動盪時代作真理與和解見證
然而,先知性的教會並非要逃避政治。「沉默」從來不是表達中立,而是一種共犯。真正的先知性參與,是在任何政權之下都堅定地宣講:公義、憐憫、真理與人的尊嚴。
這樣的教會不替任何黨派拉票,而是塑造信徒的良心,使他們能夠以信仰的眼光分辨是非,在公共生活中成為誠實與仁愛的公民。它也以自身的群體生活,活出和解的見證──讓世人看見,基督徒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卻仍在基督裡彼此相愛。
布魯格曼提醒我們,先知的任務不只是批判現實,更是「想像一個上主真實臨在並作為世界主宰的世界」。這樣的想像,正是台灣破碎社會最迫切需要的盼望。
近幾年的政黨對立衝突,留下的不只是政治傷痕,更揭露了我們社會的道德裂口。如今,教會面臨抉擇:要繼續反映社會的分裂,還是要成為醫治分裂的力量?
赫舍爾曾說:「善的對立面,不是惡,而是冷漠。」教會若陷於冷漠,便失去作為上帝百姓的靈魂。先知性的群體不能袖手旁觀,而要以上帝的心看世界──敢於悲傷,敢於說真話,也敢於在仇恨之中實踐愛。
台灣今日需要的,不是某黨某派的教會,而是有先知性、能憐憫、敢作夢的教會。唯有這樣的教會,才能在政治的風暴中,重新成為國家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