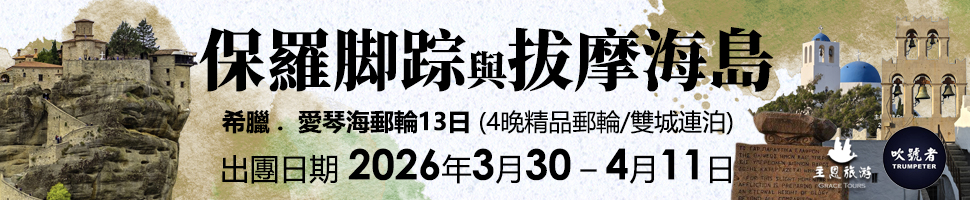◎楚雲(牧師)
1952年,上海外灘。
撲滅火種的行動從這裡展開。七十多年後,我來尋覓那烈焰的餘溫。其實,我尋的,是一道從未熄滅的火焰。
江西中路320號,一座新古典風格的四層樓建築。兩道窄門,面向僅容兩車交會的街道。這裡便是昔日生化藥廠的辦公處。
站在街角,我凝望倪柝聲最後進出的那扇門。那裡,是他失去自由的起點;前方,等待他的是二十年囚禁,直到命終。

拒屈從政治被推向風口浪尖
1952年4月10日,他的一生被推向風口浪尖。當天,一群來自東北的執法人員走進藥廠辦公室,停留約半小時,在職員與倪師母張品蕙面前,強制帶走倪柝聲。現場沒有喧嚷,眾人以為他只是被請去交代經營狀況。那時正值「三反五反」運動,私營企業首當其衝。
生化藥廠被控「竊取國家資財」。新政權執行政策雷厲風行,短短數月間,上海竟有近千位企業家自殺。新市長陳毅感嘆:「又有人空降跳傘了。」這座曾號稱遠東金融之首的大都會,成了全國政治風暴的中心。
身為生化藥廠董事長,倪柝聲無法迴避衝擊。起初,他為顧念教會同工的生活困難,放下領袖身分,參與企業經營,以補助傳道所需。這舉動卻引起教會長執的誤解,甚至要求他暫停事奉。更出乎意料的是,生化事業竟成為他被控的罪狀。
其實,真正的原因並非經濟問題,而是信仰。倪柝聲拒絕屈從政治干預,令當局不滿;而一些懷異心的宗教人士乘勢排擠,企圖奪取領導地位。裡外夾擊,終至不可逆轉──摧毀倪柝聲,勢在必行。
他被押入徽寧路第一看守所,歷時四年,外界無從得知情況。當局藉此期間密集編造罪名,為最後審理鋪路,務求一錘定音。

1956年1月29日夜,主日擘餅後,南陽路聚會處多位核心同工被捕,包括汪佩珍、李淵如等人。翌日,福州路天蟾舞台召開兩千五百人控訴大會,宣布破獲「倪柝聲反革命集團」。
教會內亦出現「猶大」。有人為自保登台指控,甚至控告倪柝聲「毒害青年」。這些控訴的語氣與內容,正顯示人在恐懼與壓力下的扭曲與軟弱。
屈枉正直、晝夜控告──這正是黑暗權勢對主門徒最狠毒的攻擊。
虛假罪名延伸為無期監禁
2月3日夜,南陽路會所又召開四千人控訴大會。許多同工與執事難敵政治壓力,被迫上台發言。
更深的惡謀已在暗中展開。附近學校舉行所謂「罪證展覽」,展示錄音、筆供、照片、書籍等偽造物證,誣指政治、軍情、金錢與私德。這是肅反運動的慣用模式──誇張、離譜、卻極具殺傷力。
忠心的人仍未動搖,但分辨力不足者,已開始迷惘。

1956年6月21日,倪柝聲被押至上海高級人民法院,靜候判決。此地離生化藥廠不過三、四百公尺。午後兩點,旁聽席上約百餘人,聚會處十二位代表列席。倪柝聲不疾不徐的走向被告席,現場一片寂靜。
審判長逐一核對罪證,倪柝聲僅簡單回應,不作辯解。他讓人想起耶穌在彼拉多面前的沉默──那是黑暗掌權之地。他知道這不是申辯的場合,只能學習羔羊在剪毛人手下無聲。
若生化廠是客西馬尼園,這裡便是髑髏地。
我經過上海高級法院門前,想像他沉默的面容。那不是懦弱,而是確信一切出於神,所以選擇「默然不語」。
這場審判本是一場演出。虛假的罪名,使審判長成了洗手脫責的彼拉多。十五年徒刑的判決,實為無期監禁。事後證明,從提籃橋監獄到青東農場、再到白茅嶺勞改場,是一層層消磨肉身的折磨。最終,他的遺體在白茅嶺火化場化作一縷青煙,歸向天際。

預感風雨欲來加緊整理信息
我重返南陽路教會舊址,那是倪柝聲最後一次向教會發聲的地方。我沉浸在歷史的回顧裡。
1948、1949年,倪柝聲的工作重心在福州。兩次鼓嶺同工訓練,是他一生真理信息發表的高峰(參筆者前作〈鼓嶺風雲──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1949年10月,新政權成立。那年年底,倪柝聲赴香港停留月餘,召開了在大陸境外最後的信息特別聚會。許多人勸他繼續留在海外,在屬靈上供應和建造眾教會,他拒絕了。這位神家中屬靈的長子,一心繫念正在經歷動盪的家。經過慎重考量,他義無反顧的重返上海。他回去的心意已決,即使他知道連猶大也在等著他。
1950年4月,正逢朝鮮戰爭爆發,「抗美援朝」聲浪高漲。倪柝聲以觀察員身分受邀赴北京,參加一項官方舉辦的基督教會議,其間當局要求切斷與西方「帝國主義」所有聯繫,且對西方傳教士予以嚴厲譴責。
這是個沉重的訊息。基督徒聚會處向來主張「一地一會」,與西方差會並無行政和經濟上的直接連繫。而要將許多愛主並為中國靈魂犧牲奉獻的西方宣教士一概視為政治特務,無論如何,這是違心之舉。
倪柝聲對當局拒絕徹底讓步,而僅僅在不違反信仰底線的前提下,表達了對執政掌權者的回應。
這當然不是當局要的答案。於是三番兩次的遊說和要脅,使信仰自由的空間逐步緊縮。威脅利誘不成功,那就在其他路徑上尋找破口。炮製各樣罪狀,掀起各地教會內外的控訴大會,給予鬥爭對象人格上致命一擊,這幾乎是最奏效的毀滅手段了。
倪柝聲預感風雨欲來,除了託付同工加緊整理信息文稿出版,同時囑咐福州海關巷執事之家的同工,將玉林山館家中的藏書,全數寄到上海福音書房,其中包括多本的英文詩歌。倪柝聲準備儘速完成詩歌編譯和創作的工作。

在火煉般的日子思想主榮耀
政治環境壓力日益緊迫,而每天睡眠不超過四小時,日夜趕工,倪柝聲靈雖剛強,但魂的重壓和身體的背負,使他瀕於崩潰邊緣。此時的倪柝聲如處在魔鬼齒縫之中,他病倒了。
有如拚盡最後一股力量,倪柝聲沒有在路的終了敗陣下來。像是越過一道大山,他完成了畢生對教會最後的貢獻,1052首詩歌本,這藏在地裡的寶貝,至今仍被許多愛主之人發現、傳唱和珍藏。
很幸運的,我投宿的地點,恰恰在昔日南陽路教會和福音書房之間的里弄裡,這間旅店的最高樓層又連接著南陽路會所,我幾乎就是下榻在當年會所的頂層。
夜間,我找出倪柝聲在那火煉般的日子裡所寫下的詩歌「祂的臉面祂的天使常看見」:
「天上雖有榮耀的冠冕,卻無十字架可以順從;祂為我們所受一切磨碾,在地才能與祂交通……
不久就無誤會怒罵羞辱,就無孤單寂寞離別;我當寶貝這些不久的祝福,我藉這些與祢聯結……」
這實在像一篇神聖的禱詞,使倪柝聲孤立無援、四面受困的時刻,仍有讚美的靈直通寶座,直達天心。這歌也應和著詩篇二十二篇彌賽亞受難的預言,使身懸十架的身軀如頂天立地的巨柱,相映著天上那榮美的臉面。
聽著聽著,我心中似乎明亮了,原來那天在法庭之中,那孤獨的囚犯並無悲苦的表情,也沒有激憤的陳詞,他比在場的任何一個人更知道何謂孤單,更了解何為榮耀。

屬靈產業已傳向全地
南陽路會所的內在空間極大,當年可容納三千人聚會,1949年基督徒聚會處由原哈同路文德里遷移到此。使用了不到十年,收歸國有。目前這裡被改建為「靜安體育館」,內有網球、羽毛球、乒乓球場等開放空間,偌大的室內場域,依然讓人直覺當年聚會的盛況。
緊鄰一座紅頂白牆的法式建築,裡面裝潢得極為華美,此處就是舊日福音書房。身處其中,心裡有莫名的感動,我幼年至今深深受益的屬靈信息,許多出自這裡。除了倪柝聲的書刊,另外也包括了「荒漠甘泉」、「馨香的沒藥」等,當然,還有1052首分散在不同版本的動人詩歌。
不遠處轉角就是哈同路(今日銅仁路),240弄文德里老會所的石庫門排屋已經拆除了,倪柝聲和汪佩珍、李淵如等同工早年就分住在附近。原地已蓋起大廈,做為一般語文教育中心。前人已逝,景物已非,但這裡曾有的屬靈產業,已傳向全地了。
生化藥廠租用的廠房,依然留在膠州路一隅,這帶給倪柝聲極大試煉的良善事業,其實是神錘練一個貴重器皿的特殊功課。美名惡名,都見證了基督不能隔絕的愛。
再次來到提籃橋監獄。不久前這裡的監管體系已遷移到滬西約一小時車程外青浦區的青東農場(昔日勞改場),這恰是倪柝聲當年判刑坐監提籃橋監獄十五年之後轉移的場所,刑期雖滿,當局不放人,並且繼續押往安徽白茅嶺勞改場服刑,期間倪柝聲曾為痛失愛妻而申求返滬奔喪,也遭嚴拒。

獄中堅定表達不放棄信仰
1972年6月1日,倪柝聲遭折磨病逝於白茅嶺。時年69歲,來到荒遠之郷,倪柝聲至終未曾再回到黃浦江畔。
我想起倪柝聲的監獄室友吳友琦弟兄的見證。他在獄中親自聽聞倪弟兄堅定表達不放棄信仰的發言,至今記憶猶新。這和當年倪柝聲準備由香港返回大陸的堅決心意,始終一致。
倪柝聲一生的毀譽不證自明。「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羅馬書八章33節)
黃浦江畔的水影倒映著一座城市繁華若夢的奇幻,從三零年代傳唱流行在這城市的人間曲調,我獨獨懷念那直擊靈魂的愛歌:「他的臉面他的天使常看見」、「有時偶是青天」……
南陽路的會所,還能回到教會的手中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倪柝聲在那如烈火近身的年日所寫下的詩歌,是最好的答案。
「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如果祢收去的東西,祢以自己來代替。」(「你若不壓橄欖成渣」歌詞選)
這是永恆的新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