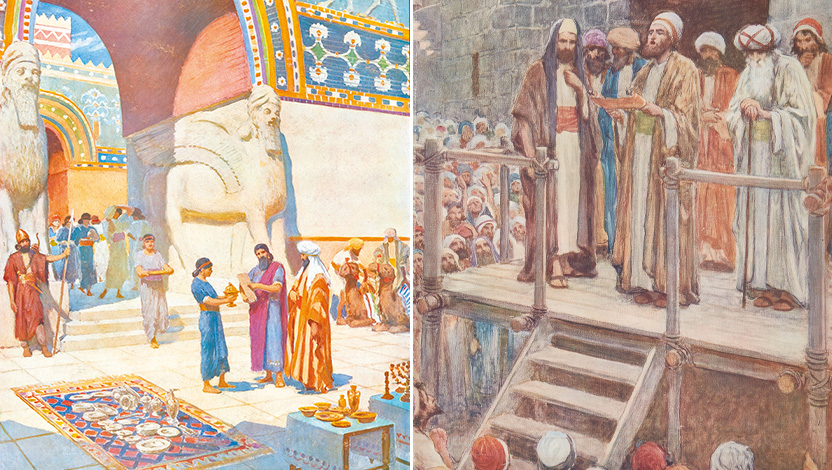◎方激
那一年,在美國東岸櫛風沐雨多年以後,年近中年的我經歷了失業的煎熬。深秋時節,為了面試一個渺茫的工作機會,我趕往新墨西哥州的科洛維斯小城。雖然靠著信仰努力振作精神,期待轉換職場跑道重新出發,但我仍然感覺自己的前程像墜入了無邊的混沌中。
在亂流中顛簸了一路的小型客機終於在阿馬里洛著陸時,已是日暮時分。飛機沒有停在登機口,而是泊在停機坪的轉角處,走出機艙的瞬間,我便置身於令人窒息的廣袤中。落陽貼著地平線斜照過來,將萬物浸染得熠熠生輝,遍地綻放的野菊花從容地隨風擺動,令人心生溫暖。我突然想起,在西語中,「阿馬里洛」恰是「金黃」之意。
在橫跨德克薩斯與新墨西哥兩州的數百公里內,唯獨阿馬里洛建有距離科洛維斯最近的民用機場,這意味著,我必須以自駕走完這最後的一段旅程。
駛出城外不久,餘暉漸暗,原本就不繁忙的公路上,車輛愈見稀少。飛馳過處,路旁的景物急速後退,令人彷彿置身於被不斷展開卻永遠不見盡頭的布景中,漸次排列的農田、風吹草低的牧場、木條圈圍的畜欄、隨風轉動的風車、堆放有序的草垛,都是布景中無比生動的元素。那些並不寬闊的清澈小河蜿蜒在沒有邊際的荒原上,在夕陽下波光粼粼。眺望極遠之處,還有綿延起伏的黛青色群山,如隔著霧氣一般地若隱若現,彷彿提醒我,由此西去,美國中部一望無際的大平原將漸漸化身為連綿的山地。
恢宏與單調並存,壯闊同孤寂共生,長久以來身心俱疲的我感覺到久違的舒緩與放鬆。彷彿獨行於天地之間,腦中或仍殘存幾分雜念,但心胸卻無可限量地開闊起來。面對著上帝造物的雄渾與偉岸,我的心中滿是敬畏。

天色愈發昏暗,直至遠近都最終融為模糊一片。科洛維斯位於兩州交界線以西十幾公里處,雖然坐落在海拔1200米的高原地帶上,地勢仍基本平坦。我到達時,已過晚上十點,幾乎所有的店鋪都已打烊。駛進這個夜色籠罩、波瀾不驚的小城時,我似乎能窺見中部處處可見的隨意與閒散。
我毫無倦意,但除了找到旅館住下,竟然別無去處,心下頓生幾分不甘。倏忽間,那個在途中盤桓許久卻被我屢次按捺的念頭,又悄悄爬回腦中。在如水的夜色中,我帶著巨大的衝動再次駛上鄉間公路,決意向著西南方向繼續前行。距此地兩百公里外,另有一座曾使新墨西哥州聞名世界的小城羅斯威爾,從少年時代初次聽聞幽浮的典故開始,我便記住這個地名,無數次憧憬著去一探究竟。
在這臨時起意的第二段行程中,前四分之一是令人亢奮的。離開科洛維斯尚不遠,仍可望見那裡稀落、閃爍的點點光亮。而在荒原盡頭的神秘之境中,究竟藏著怎樣的未知?令人興奮莫名的揣測讓我的額頭微微沁出了汗珠。
行過一個叫伊麗達的荒涼小鎮時,我意識到自己已是飢腸轆轆。在一間連著加油站的小賣店門前停下,我預備給車子加滿油,再去買一份簡單的晚餐充飢。停車開門的片刻,我瞥見幾道無法形容的銳利眼神向我直射過來,幾個彪悍、孔武、帶著警覺甚至敵意的印第安男人正站在路邊。其中一個長髮披肩、臉色暗沉、上身套著件皮製馬甲的年輕人,還向我慢慢走來,他一邊向同伴做著手勢,一邊將手背到身後摸索。剎那間,我的腦中閃過無數可能,心跳幾乎破表,趕緊發動引擎,想要倉皇逃離這塊印第安人的保留區。
無人追趕上來,但我的眼睛卻始終不敢離開後視鏡太久。在濃重的夜色中,小鎮雖已被遠遠地拋在身後,我卻仍舊緊踩油門向前猛衝。潛意識中,我生出愈來愈強烈的悔意,感覺這無邊無界的黑暗荒原正化為變幻莫測的大海,而我只是藏身在其中的某條小船上,任由漫漶的海水從四周洶湧而至,彷彿一個浪頭拍來,便能將我無情地淹沒、吞噬。
我擰開音響,鄉村音樂立刻塞滿車內小小的空間。一位叫不出名字的男歌手襯著簡單的吉他和弦低聲吟唱,曲調沉穩、低洄,濃重的鼻音淹沒了歌詞,每一個尾音都被他誇張地放大和故意地扭曲了。這或許就是鄉村歌謠的精髓吧,不去負載複雜的元素,只是唱些眼前的三長兩短、心中的某個念頭,譬如當下,他可能正在吟唱前方夜色中的這條漫漫長路。在心理作用奇妙的借代與轉換間,歌聲牽引著我的思緒飛揚起來,令我回憶起當年如何在人生低谷中遇見上帝,而上帝又如何引領我走出心靈的困境。
身後遠遠響起一長串火車的汽笛聲,不知從何時起,一條鐵軌開始出現在公路的右側。黧黑的鐵軌筆直地向前延伸,將深海一般的荒原映襯得更加不著邊際。一輛拖著十幾節車廂,載滿了煤或某種礦產品的老舊火車,咣噹咣噹地從我身邊駛過。寂靜被打破了,身旁突現的旅伴給我帶來幾分安全感,催促我不再顧影自憐。我將油門踩得更重一些,幾乎保持與火車同步的速度,與它在黑夜中並行向前。
然而,並未太久,公路與火車鐵軌的間距便被拉大了,前方的鐵軌不再與公路平行,而是逐漸偏行向右,直至駛上一座低矮的鐵路橋。再過片刻,當我從橋下穿行而過時,火車汽笛也長鳴一聲,徹底劃破黑夜的寂靜。在作別的信號中,那十幾節車廂從我的頭頂向著左前方繼續咣噹咣噹地遠去了。

大地復歸寧靜,一個有關保護新墨西哥州自然環境的告示牌在窗外一閃而過。在浩渺的荒原中,我腳下的公路仍向著望不見盡頭的遠方延伸,彷彿大海中被遺忘的一葉孤舟。音響裡的鄉村民謠換了一首又一首,無論歌手是男是女,聽來都是如此相似。我漸生倦意,索性關了音響,搖下車窗,任由深秋的晚風裹挾著荒野的氣息撲面而來。那氣息混合著乾草的澀、夜露的濕,還有牲畜糞便淡淡的腐臭味,散發著我從未領略過的、嗆鼻的新鮮,它奇妙地安撫著我不久前仍慌亂不安的心,讓我更專注於外面的世界,也將目光投向更深遠的前方。
在深不可測的黑夜裡,荒原的景象正在悄悄改變,山巒越來越密集地出現,黯淡卻依然雄偉;斷續間也聽得見潺潺的水流聲,微弱又執拗不息。上帝彷彿在提醒我,只要仍有生命與氣息,萬物就皆有改變的可能,世間的風景如此,人生的風景又何嘗不是?
等到路邊再次出現加油站的招牌時,又過去了一個多小時。破敗的加油站前吊掛著一盞老舊的路燈,在風裡搖盪,亮著忽明忽暗的光,在地面上拋下一個個變形的光圈。這一次,我在稍遠處停車,沒有急著熄火,而是警覺地遠遠打量四周的動靜。唯一的加油泵上無精打采地搭著生鏽、老舊的加油槍,拖拽著一條乾裂的長皮管,彷彿是盤踞世上、僵而不死的千年古蛇。加油泵的後方立著一間小小的舊木屋,應該是久經沙塵侵襲的荒廢民宅,門前還有露台,露台上居然橫放一把木製搖椅,在風中輕輕搖擺,提醒路人此處並非靜止的畫面。木屋的正面用紅色的油漆刷了大大的「gas」,也早已斑駁不堪。
我謹慎地觀察了一會兒,不見任何動靜,於是鼓足勇氣開車近前,向著木屋喊了兩聲,仍沒有任何回應。我這才關了引擎,拔下油槍,塞入車後的油箱口,再轉身去車上找皮夾。不曾想,翻遍了書包,我卻無從發現皮夾的蹤影,甚至抓了書包在路燈下裡外翻找,仍是遍尋不著。我努力搜索記憶,想起最後一次翻皮夾是在科洛維斯的旅館前台,無疑,它一定是被落在那裡了。
我坐回車裡,眼看著不足一格的油量,再度深感頹唐與絕望。枯坐默禱十幾分鐘後,我決定繼續向著羅斯威爾前行。在導航儀尚未問世的年代,地圖是旅人異地行路的基本指南,然而,抓著一張並無太多細節的地圖,我終究無法確定自己究竟身在何處。我反覆心算行車的時間與速度,確信此地已離羅斯威爾不遠,唯有禱告期冀所剩無幾的汽油能夠支撐我將車子開到那裡。
再向前行進了半個多小時,油箱淨空的警告燈亮起來了,我的思維幾乎停頓,只知道機械地繼續行車。只要車子能動,開上一米就算一米吧,我想,在空寂的黑暗荒野中,動比靜總能給人帶來更多的希望。
萬籟俱寂中,我終於聽見前方傳來輕微卻是持續的聲響,汩汩流動,源源不息。我憑著直覺斷定,這是從北方逶迤南下的佩可斯河。根據行前從旅行手冊上讀到的信息,在這條公路與佩可斯河的交界處,沿河向南行約一百公里,便是著名的卡爾斯巴德溶洞;地圖更清楚地標示出,只要能在這條公路上望見此河,羅斯威爾便真的已相去不遠了。
寬闊的佩可斯河谷橫亙在公路的橋底,夜色中,河水泛著依稀的白光。橋下另有一條小路沿著河谷蜿蜒延伸,路牌依稀指明,向北通向澀湖野生動物保護區,向南則通向無底湖州立公園。雖然不知道小路最終將延伸至何處,但我仍然在瞬間決定繼續遵從上帝無聲的召喚,我向右方調轉車頭,徐徐駛上小路北去的一方。
行至此處,面對可能已經無法輕易脫身的困境,驅使我繼續前行的動力已不再是一個具體的地點,而是對找回失落一切的渴望。我渴望找回最真實的自己,找回初信時對上帝的全然信靠,找回曾有的平安與喜樂;我仍期待著在山重水複之處遇見峰迴路轉,就像當年遇見上帝,而上帝又照著我的本相全然地接納我。
又行駛了大約二十分鐘,在繞過澀湖保護區不久後,突然之間,汽車像是老人咳嗽似地喘息兩口,徹底地拋了錨。無疑,我此行的終點就在此處了。手錶的時針指向午夜兩點十分,我拿出手機,卻無法接收任何無線訊號。事實上,在這樣的時間、地點,我根本不知道應該如何求救、向誰求救。我套上外衣,跨出車外,在空曠無人的荒原中依稀辨認遠近山的輪廓、水的行蹤;抬頭望天,更驚喜交加地看見滿天的繁星,令我不由得聯想起那閃耀在歲月長河中永恆不滅的信仰光芒。在深秋的夜晚,我從未見過如此璀璨的星空,甚至無從記起,自己上一回仰望星空是什麼時候。
此刻,我的心徹底回歸平靜,突然明白了所謂交託的真正意涵,明白了上帝為我安排此行的意義所在。一無掛慮,所以心安理得;一無所有,所以無謂失落。我不再感覺自己置身於某個孤獨無援的境地,反而像是回到久違的家中,充溢在我心中的,不是懼怕,不是煩擾,不是懷疑,而是某種頓悟後的全然釋懷,恰如拍打海岸的潮水一般,它們一陣陣地漫過我的頭頂,襲遍我的全身。
我被無比強大的睏意與前所未有的輕鬆感同時緊緊地包裹著,在四顧無人的荒野間和衣臥倒,盡情舒展著在車裡被摺疊許久的雙腿。浮現在我眼前的,不是黑暗,不是荒野,卻是輝映在阿馬里洛黃昏中的那片醉人金黃。在一方山水環繞間,在一片星空閃爍下,我頭枕著一把荒草,寧靜而坦蕩地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