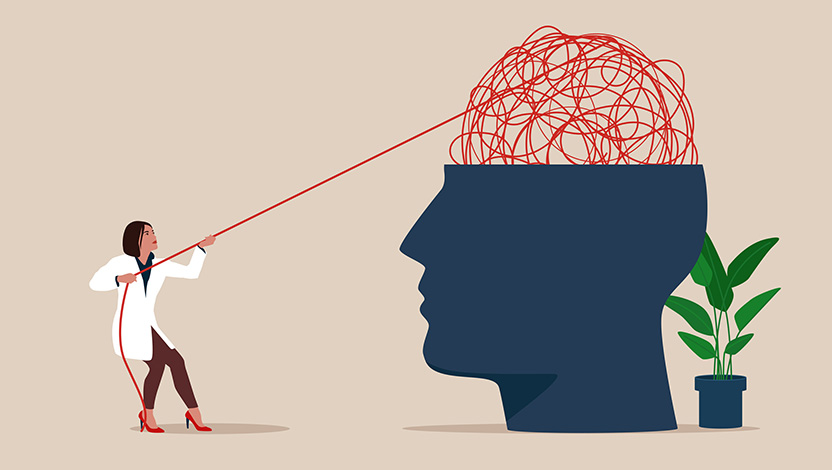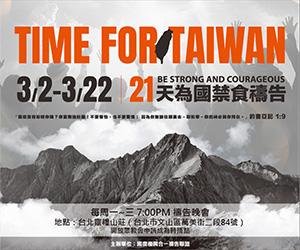◎高佳慧(美國加州柏霖甘國台語第一長老會會友)
很長一段時間,我把「自由」誤解為「遺忘」:把受傷、委屈與黑暗面通通從腦海與心裡抹掉,心就會輕。可現實像被拉反方向的橡皮筋——越想忘,越是拉扯。直到我讀了主的話:「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翰福音八章36節)。
越想忘記傷害 情緒越是拉扯
如果自由不是「不再記得」,那它像什麼?我想到:在仍記得的情況下,不再被牽引。
這個問題在一次線上查經會後變得具體。那天,幾位姐妹分享著過去受傷的經驗,我也說了自己在職場的挫折。巧的是,有位曾在同一單位工作的姐妹,也見證了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聚會中我得到許多安慰與鼓勵;散會後,心裡卻有個聲音追問:「你會不會把『受傷』的分量,放得比神的榮耀還重?」
「榮耀」在希伯來文有「重量」之意。我開始檢視:到底是我和我的感受占住心中的重量,還是對神的順服更重?
表面上,我似乎做了正確選擇:不與人計較、選擇沉默,把審判交給主(羅馬書十二章19節),相信祂是我四圍的盾牌(詩篇三篇3節),把話語權交託給神、等候祂的公義。然而我也發現:內心仍緊抓那份羞辱,像握著一個死結。
我真的交託了嗎?還是把「沉默」當成盔甲,卻讓傷口在裡面發炎?主耶穌「被辱罵不還口;受苦也不說威嚇的話,只把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的主」(彼得前書二章23節)。那是完完全全的交託,而不是「情緒表面歸零、心底仍抓住」。我的糾結,正暴露出我未曾全心交託;更糟的是,我是否也在軟弱裡暗暗生出自義?
在「神的形像」與「人的罪性」之間掙扎,我需要萬軍之耶和華的幫助,學像基督,才能得著真正的自由。
拒讓傷害定義 讓主回到敘事中心
在邁向自由之前,也許先從命名開始。不是粉飾,不是否認,而是如實承認:「那件事確實發生,我的心確實受了影響;我也有盲點與錯誤。」聖經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羅馬書八章1節)。當事件被如實命名,它就能被歸檔:承認其存在,卻拒絕讓它繼續定義今天的我。
接著,把重量移交:「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得前書五章7節)。卸下不是丟棄記憶,乃是把主權放回主的手裡——「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後書三章17節)。
再往前一步:當基督站回敘事中心,故事就被改寫。詩篇說:「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主不是要我先把情緒整理到完美才配親近祂;是祂的同在安靜了情緒,給我面對的力量。於是我發現:陰影會褪色——不是瞬間消失,而像退潮:傷害仍在,卻不再主宰。當我重述那段歷史,焦點從「我曾多痛」慢慢轉向「祂如何與我同在」。主詞換了,心的重心也跟著換位。
赦免也因此有了另一種面貌。它不是硬擠出的口號,而是在同行中自然長出的果子(參加拉太書五章22–23節)。當我把正義與辯白交給主,「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就變得可信——不是因為痛變小,而是榮耀變重。
我開始自問:今天我在社群的一段敘事、心裡的一次複誦,是讓傷害加重,還是讓基督加重?哪個更重,哪個就更像主宰。
握緊的羞辱 再次放回祂手裡
向前走,保羅提醒我:「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我明白,這裡的「忘記」不是失憶,而是重新排序:讓基督與祂的呼召成為主旋律,其他聲音成為和聲。
神也說:「不要記念從前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以賽亞書四十三章18–19節)。新事不是抹去舊事,而是把舊事放進新的座標裡看:「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於是,我把自由理解為:痛仍可被記起,但不再牽引方向;歷史仍可被述說,但主詞已經更換。我仍有軟弱,仍會在夜裡反芻委屈;就在那些時刻,主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哥林多後書十二章9節)。我便把那一點握緊的羞辱,再一次放回祂手裡──不是一次到位的壯舉,而是日復一日的小小歸還,逐漸贏得在主裡的自由。
你也在問:「我是否把受傷的重量,放得比神的榮耀還重?」也許可以與我一起做一個簡短的禱告:
主耶穌,我承認這些事確實發生,也承認我仍被牽引。求你把榮耀的重量放回我心的中心,教我把審判交給你,把今日交給你。讓我在仍記得中,學會自由地前行。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