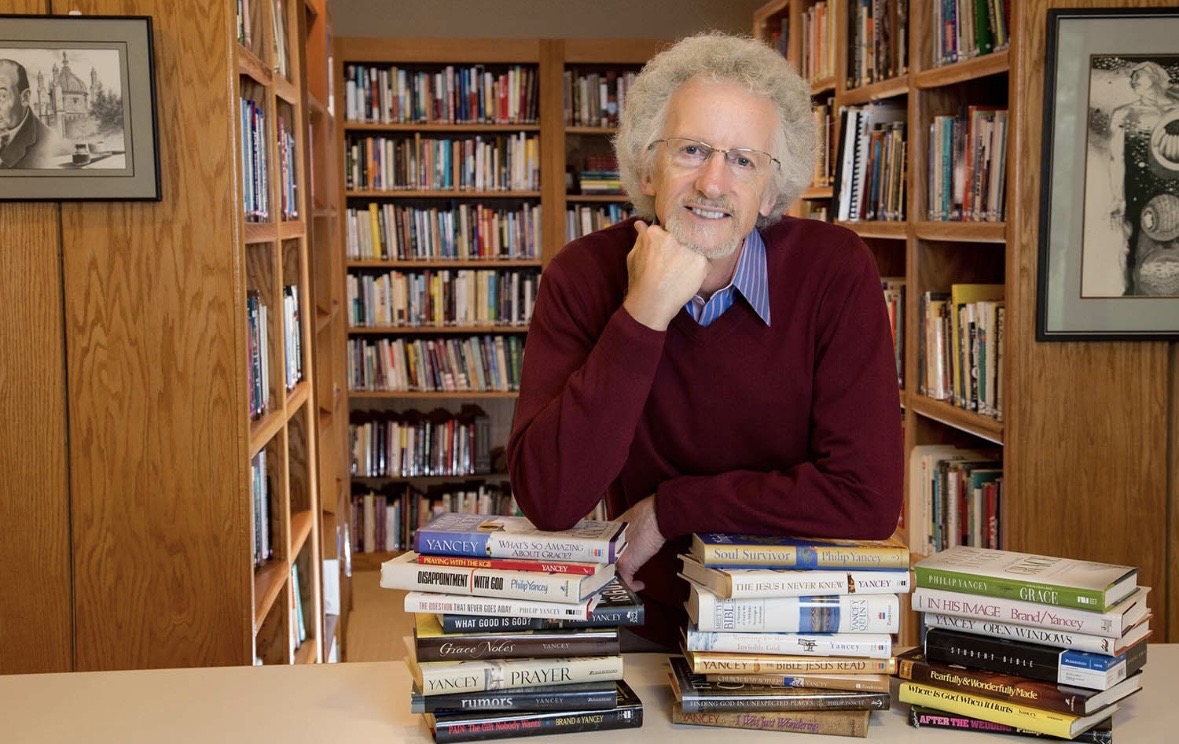◎陳麗玲
去年夏天,八十歲的媽媽因右腳骨折緊急開刀,幾天後返家休養。意外發生讓她顯得很沮喪,住院那幾天也略顯急躁,因為她向來都是照顧別人,喜歡動手自己來的人。弟弟、妹妹(婿)們合力準備了各樣輔具並加強無障礙設施,週間白天由我負責照料,晚間和假日則是大家互相支援。
共同照顧創造良善關懷空間
媽媽從一個照顧者變成被照顧者,心態上也調適頗快。家裡開始每天都有訪客,有久違的親屬、鄰居和好友;人多的時候,就在媽媽床邊圍坐成一個圈,她會不厭其煩地重述她怎麼受傷、開刀以及我們如何分工照顧她。
媽媽懷著感恩的心,相信自己會很快好起來,她也經歷著各種恩典。常常電鈴響了,有人送來補品、水果就離開了。媽媽行動不便但善用電話,慰問生病的親友和獨居的長輩,而就在這段接待訪客與應門的過程中,我更深地認識媽媽是如何有愛的關懷人,以至於在她受傷後,這許多人的愛湧流回到她身上。
廚房的餐桌常擺滿了弟弟和妹妹們烹煮的美食,媽媽則是在樓上臥室用餐。這讓我想起了缺席的父親。7年前爸爸抗癌期間,我們回家合力照顧時,都是媽媽為我們準備餐食。父親後來在醫院的安寧照護下辭世,也是被一份濃濃的愛簇擁著。醫師和護理人員,從陌生人變成一家人,我們形成一個彼此相愛、共同照顧的群體。
在盧雲所著《最大的禮物》寫道:「共同照顧是群體生活的基礎。在一起,我們帶這些受苦的弟兄姐妹,到休息、醫治、安歇之處。」在一起,我們可以創造一處良善的關懷空間,不只為了接受照顧的人,也為了付出照顧的人。

敞開負傷記憶是得醫治開端
媽媽在家養傷期間,她與許多親人好友的對話,就是如此建構起一個空間,讓彼此敞開那些過去受傷的記憶,不帶恐懼地將它們揭露出來。然後彼此接納、互相支持。
如同盧雲在《記憶的治療者》中所言,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醫治者。當我們願意敞開負傷的記憶,就是得醫治的開始。「我們承繼故事,一個需要被訴說的故事;透過這故事,許多我們每天聽到的痛苦傷害,能因此不再孤立無援。醫治代表的是揭露出人的傷痛乃是與神的受難最親密地連結在一起。」
當年在病床邊目睹爸爸的身體受摧殘,灰心喪志、空洞無助的眼神。內心的痛苦迫使我轉向被釘十架的耶穌,我在父親身上看見受苦的基督。我憂傷痛悔地為父親的靈魂得救禱告。就在幾次化療、出院、急診室等病房、住院,反覆折騰的循環中,伴隨牧者的關懷探訪,教會弟兄姊妹的守望代禱。最終爸爸轉回家裡所在縣市的醫學中心接受安寧照護,兩週後他在病房由牧師施洗,安息主懷。
感恩於醫學中心的關懷師(牧師)與教會同工陪伴我走過父親臨終最後一哩路,後來我利用暑假與喪假參與了安寧病房的探訪。我看見了牧師做為一個服事者,如何在病房中與病患(家屬)建立關係,讓對方願意說出自己的故事、提出問題。在傾聽、同理和接納的同時,把這些故事與神的故事連結起來。
「為什麼這樣的事會發生在我身上?」當一切突然改變,意義的問題重新臨到,讓人窒息。照顧不能再回到正常生活的人,其實是在一起尋求「新的意義」。當病人回顧過往的歷程,服事者支持並引導他找到生命的意義。
例如:有一位患者是開回收場的,牧師於是連結到創世記的內容:上帝創造萬物是各從其類,如同他做資源回收也是各從其類。就這樣每一次適時地帶入神的話或是一首詩歌,一篇禱詞,創造出一個人與神可能相遇的空間。在安寧病房我看見了一個又一個病人在臨終找到了生命的意義,與神和好,對恐懼放手,以盼望跨越死亡。
愛能穿越時間限制帶來希望
回想7年前父親經歷病痛的折磨,最終得到救贖的恩典。死亡只是暫別,不是永訣。永生的盼望取代了生死兩茫茫的縹緲絕望。「這愛不是對已逝者的傷感回憶,而是一股支撐我們的真實力量。藉由記憶,愛穿越時間的限制,為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刻帶來希望。」(記憶的治療者)每當我和媽媽、弟弟、妹妹與家人們歡聚圍繞著餐桌,缺席的父親以一種嶄新的方式與我們同在。
這使我想起我們作為神的兒女在領受聖餐時,「圍繞一張擺了餅、酒和聖經的桌子,是為了提醒彼此記得我們所承受的應許,進而鼓勵彼此在盼望中繼續等待。」當我們受邀來到聖餐桌前,不僅是紀念耶穌的死亡,同時也歡慶耶穌的復活;因祂的死亡而悲傷,同時也因祂的復活而喜樂。救贖的恩典,就藏在記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