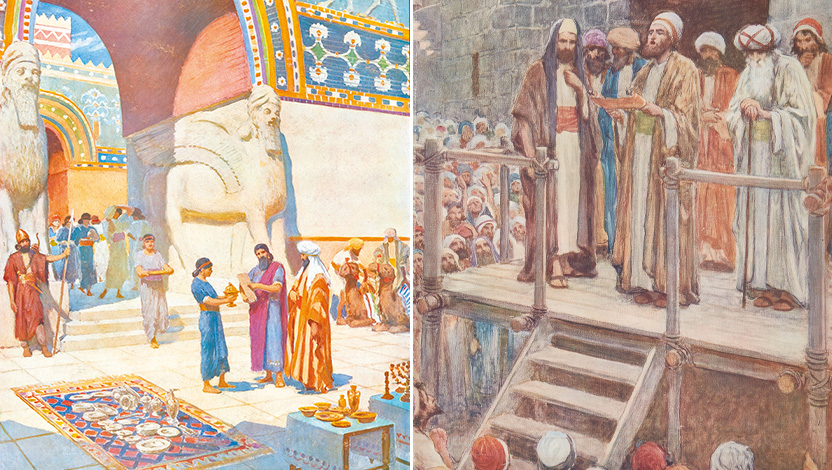◎語聆
每年的12月,空氣中瀰漫著歡樂的氣氛。商場、超市裡循環播放著熟悉輕快的聖誕旋律,街道兩旁的燈飾被點燃,人們互道聖誕快樂,彼此祝福──這是一個應該快樂的季節。
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越來越清楚並非每個人在這個季節裡,都能走進快樂的心情與音樂裡。
聖誕的燈飾尚未完全收起,新年的日曆本卻已翻開。站在這樣一個交會點回望,我發現,那些沒有被抒發的悲傷,並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自動消失。
1.戰場鐘聲
過去這一年,身邊與遠方的好友經歷分離與失去。有人失去至親,有人送別伴侶,有人在漫漫長夜裡照顧年邁的父母,有人為重度抑鬱的成年子女流淚,有人失去健康、走在抗癌路上,有人因病菌侵入下半身癱瘓……
是在這樣的時刻裡,我第一次聽到歌手Sandra McCracken重新詮釋的《我聽見聖誕日響起的鐘聲》(I Heard the Bells on Christmas Day)。那並不是一首讓人立刻感到安慰的歌。旋律沒有急著把人拉出深淵,反而像是陪著人坐在谷底,讓黑暗完整的被看見。
「當那一天到來時,整個基督世界的鐘樓敲響,傳遞著不間斷的歌聲──世上平安,善意臨到世人。」
這首詩歌是由1863年美國詩人亨利‧華茲華斯‧朗費羅在南北戰爭時寫的詩〈聖誕鐘聲〉改編而成。雖然當時充滿戰亂,但鐘聲帶來平安與希望,傳遞和平降臨的信息。
情感豐沛的朗費羅一生經歷許多悲劇。當時57歲的他,妻子因衣裙不幸著火灼傷,隔天去世。朗費羅本人因為臉部燒傷過於嚴重,無法出席妻子的葬禮。喪偶的他獨自撫養6個孩子,最大的兒子因在前線作戰受傷,幾乎全身癱瘓。朗費羅有一段時間曾經因為過度悲痛,考慮住進精神療養院裡。
目睹當時國家南北方自相殘殺的撕裂,加上他內心的失調與哀傷,朗費羅寫下了這段文字:
「在絕望中,我低下了頭;『世上沒有平安』,我說,因為仇恨太強,它嘲弄那首歌,那首唱著『世上平安,善意臨到世人』的歌。」這不是誇飾的絕望,而是一種被現實一寸寸磨平的信念。當仇恨顯得如此具體、如此有力量時,任何關於平安的語言,都像是一種嘲諷。人低下頭,不只是因為悲傷,而是因為再也不知道該向哪裡仰望。
但是緊接著下一段帶來鐘聲傳遞的信息:「這時,鐘聲敲得更響、更深沉;上帝並沒有死,祂也沒有沈睡;我在聖誕節那天聽見鐘聲,它們奏起古老而熟悉的頌歌,那野性又甜美的詞句一再迴響,述說著:世上平安,善意臨到世人。」
正是在這樣的深處,鐘聲才顯得如此突兀。它不是從勝利而來,而是從瓦礫之中響起;不是為了證明痛苦是錯的,而是宣告痛苦沒有最後的發言權。那鐘聲並沒有消除戰爭,也未立刻醫治創傷。它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敲響,像是在替那些無法再說話的人呼吸,替那些被壓碎的心臟維持節奏。鐘聲的釋放感,不在於問題被解決,而在於──有人仍然為世界敲響希望。
這是一首在哀傷中的人寫下的詩歌。或許正因如此,讓這首古老的聖誕歌,引起共鳴,因為它承載了喜樂與憂傷之間的那種撕裂、拉扯與張力。
在人類的故事裡,無論個人或者集體的記憶,我們會發現許多時刻裡,憂傷與喜樂相依並存,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因此,穿越絕望和懷疑,鐘聲依然在響。鐘聲不是逃離痛苦的出口,而是在痛苦中站立的證據。它允許人暫時不需要答案,只需要知道:在最混亂的時刻,仍有一個聲音提醒我們,崩壞尚未結束一切。
另外一首我喜歡的吟唱詩人Leonard Cohen 的作品《Anthem》裡副歌歌詞:「敲響那些仍然敲得響的鐘,忘了你那完美無瑕的獻祭,萬物之中,都有裂縫,一道裂縫,光,就是從那裡照進的。」
在一個混亂、失序與荒涼的戰場中,鐘聲響起,是一幅什麼樣的景象?也許那不是壯麗的畫面,而是一個孤獨卻頑固的聲音,在煙硝未散的空氣裡持續震動。它不否認死亡,不粉飾破碎,只是在廢墟之上敲響節奏,讓仍然活著的人,記得自己還能聽見。

2. 病床喪鐘
今年陪伴一位教會弟兄抗病,深刻體會到苦難的無常。我無意間發現楊腓力兩年前出版的《Undone》(暫譯:徹底崩解),這是他根據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的《遭遇患難時的靈修》,以現代語言重譯的靈修筆記。書中聚焦對疾病與苦難的反思,在痛苦中重新審視人性的軟弱、上帝的良善、造物主的主權,以及對復活的永恆盼望。
這本書像是一場跨越400年的對話。
詩人、牧者約翰多恩在1623年的大瘟疫、疾病、死亡陰影中,寫下靈修筆記;而2020年世界爆發新冠疫情,楊腓力在全球恐慌、隔離、死亡數字節節攀升的時空下,重新翻開多恩的筆記。他發現四世紀前的多恩、躺在病床上問的問題,也是現代人正在問的問題:
為什麼是我?
上帝在這裡嗎?
如果我不痊癒呢?
如果我失去一切呢?
諷刺的是,就在這本書編輯期間,楊腓力本人被確診罹患帕金森氏症。他忽然體會到多恩在筆記開篇那段話的重量:
「人類的處境變幻不定,而我此刻既是健康的,又是病了的。」
那是一個瘟疫肆虐的年代。喪鐘每天響起,人們不知道下一個是誰。
當年在隔離中、在病床上的多恩,聽著喪鐘,心裡想的是:「會不會,下一次敲的,就是為我?」
詩人沒有逃避這些念頭,選擇用文字把每一個階段記載下來:身體的不適、心裡的恐懼、對上帝的質問、對死亡的凝視。感覺上好像不是「很屬靈」的文字,卻是多恩極度誠實的信仰紀錄。
筆記中有一篇以《盼望》為題的篇章,多恩從病中的觀察出發,反思盼望的真義。他說盼望並非一種情緒上的樂觀,而是一種在不確定、延宕與無法掌控中仍然持守的屬靈姿態。他注意到,疾病並不會遵循秩序:有時病情急轉直下,有時恢復緩慢無聲;自然的節奏──播種、開花、結果──在病痛中被打亂,人只能等待,卻無法催促。正是在這樣的失序中,人被迫學習何為真正的盼望。
寫作生涯超過半世紀,一直以苦難為書寫主題的楊腓力,從多恩身上學到:當疑惑來臨時,我們需要重新檢視自己的選項。多恩與上帝摔跤的過程中,他的問題從「誰造成這場疾病?這場瘟疫?為什麼?」的默想,慢慢轉移到另一個方向:「我是否願意在這場危機中信靠上帝,面對疾病所引發的恐懼?還是,我要在苦毒與憤怒中轉身離開祂?」
這讓我回想陪伴弟兄的日子裡,當病菌突襲,他一次次進出急診室,數度從鬼門關回來,期間叩問上帝的問題並非「為何是他」,而是這一次上帝有什麼功課要他學?他信靠上帝的程度有多深?他將病床當作祭壇,身體當作活祭獻上。
原來準備好完全放手的多恩,以為自己即將離開人世,沒想到恢復健康,又多活了8年。
但是那場患難的經歷讓他的信仰更深邃。而面對自己的慢性疾病,楊腓力說願自己成為「苦難」篇章的美好見證。

3.藍色聖誕
“Blue Christmas”是一個屬於北美教會的傳統。牧者們選擇在12月21日,這一年中黑夜最長的一天舉行「藍色聖誕」聚會,像是為悲傷的人預留空間的聖誕儀式。
去年聖誕前夕,我參加了一場美國教會的藍色聖誕聚會。整個聚會約一個鐘頭,在場的大多是灰髮的長輩們,每個人都帶著一份故事前來。或者述說,或者沉默,我們在一個被恩典圍繞的空間裡,靜默、反思,與哀哭的人同哀哭,感受那份不張揚,卻真實的神聖同在。
那天牧師短講的信息,出自詩篇第二十二篇。
這是一首深刻的彌賽亞詩篇,作者大衛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大衛從苦難出發,述說自己極深的痛苦,以及那種彷彿被神離棄的感受。在詩篇中,他也預言了一千年後,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受難景象。
牧師說聖經中,有一個我們常常忘記的模式:上帝最親近的僕人,往往走過最漫長的沉默。
亞伯拉罕等候了數十年。約瑟在監牢中消磨歲月。摩西在米甸的曠野住了四十年。
哈拿在主面前痛哭。耶利米流淚如河。而大衛那位合神心意的人,寫下了詩篇第二十二篇。
「沉默,不等於被棄絕。延遲,不等於拒絕。黑暗,也不等於距離。」牧師說,「有時候,上帝在沉默中,比祂發聲時,更為接近。」
因此,當耶穌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祂也同時宣告祂正是大衛筆下那位受苦的義人。詩篇二十二篇正是主耶穌的故事,是祂來到世上受苦,要完成使命的故事。
「如果你今天正停留在詩篇第二十二篇第一節,感到被遺忘、被離棄、或被壓垮,」牧師溫柔的說,「請不要忘記,主耶穌,就站在你身旁。」
「祂承擔了第1節的呼喊,好讓我們能分享第31節的勝利。」

喜樂,不是被強行堆疊出來的快樂。它可以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奇蹟。
朗費羅在失去愛妻、國家陷入內戰的時刻,低下頭承認:「這世上沒有平安。」
我終於明白,鐘聲響起,並非為了掩蓋悲傷。鐘聲在黑夜裡響起,是因為人們在最深的裂縫中,才會大聲呼求、祈禱、盼望;而在這些聲音之中,我選擇相信──即使如此,上帝從未離席。
回首過去一年,我陪伴雅各弟兄走過病痛的幽谷,也感同身受好友的喪親的淚水與哀傷。正是在這些時刻中,讓我體會到鐘聲的真諦:它不是遠方的迴響,而是內心的召喚。
歲首。
雨夜。
桌前。
燈下。
在靜默之中,我回溯這些脆弱卻美麗的片段,也驚覺,一絲光,已悄然滲入。
新年伊始,我不急著為新的一年籌劃,反而願意帶著鐘聲前行──在破碎之中仍然聆聽,在靜默裡不放棄呼求,在尚未看清全貌之前,選擇信靠。(本文由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提供)